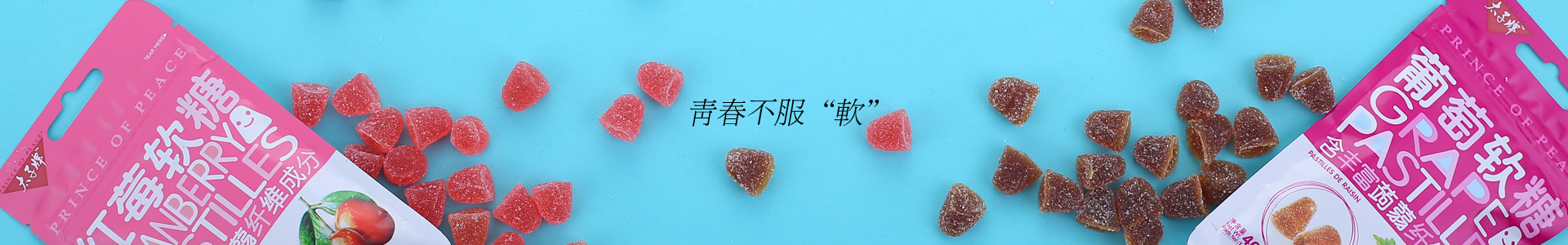新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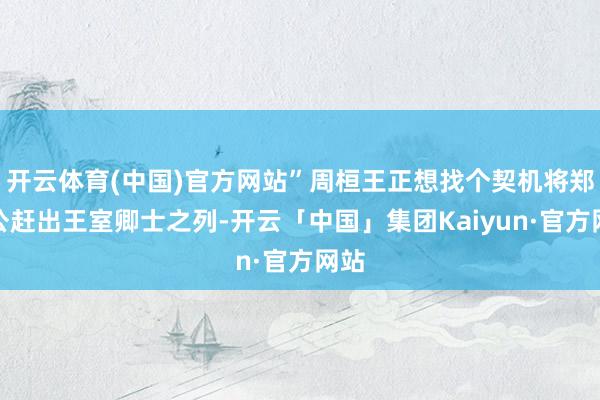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接上篇
周平王五十一年(前720年)初,周平王病重不治,在雒邑王都驾崩;而周平王驾崩时,周太子狐尚在郑国‘学习’,并不在雒邑;获得周平王弃世的音问后,太子狐立即由新郑赶回雒邑,准备为父亲举哀,然后再秉承王位。但太子狐一齐震憾、又哀伤过度,在回到雒邑后不久就病逝了,没能登上皇帝之位。
史册中莫得纪录太子狐是否有女儿,他灾祸弃世后,王室卿士们便拥立他的侄子、周平王前任太子泄父之子天孙林为新任皇帝,即周桓王。
周桓王还为天孙之时,就很看不惯郑庄公的罪责霸道之举,合计王室太过于放浪郑国了;比及我方继位后,更是不想再让郑庄公陆续摆布王室政务(司徒)、以为郑国日后行事之仰仗。于是,刚刚继位的周桓王便让虢公忌父入朝,准备让他接替郑庄公,主握王室政务。
郑庄公得知周桓王的‘换马’举动后,为了警告、恫吓王室,便在以前四月,命郑国医师祭足带领郑军插足了温邑(当先锋未属郑,且王室在当地还有大片农田),收割了属于王室的麦田;以前秋天,郑国戎行又起程王畿,割取了成周隔壁的大片稻田。
张开剩余91%郑国此举,让年青的周桓王脑怒不已,但因为少量稻麦就和郑国开战,这难免也有些小题大作念了;况且,当初周室东迁,还是靠晋、郑、秦等国的松懈协助、扶握,是以王室智力在雒邑驻足。因此,周桓王想虑再三后,还是忍下了连气儿,莫得和郑庄公巧合冲破。
不外,从此之后,周、郑之间仅剩的少量香火情(郑庄公与周平王都是周厉王的曾孙,在诸侯国之中,郑国与王室的关联正本最为亲近),也因为郑国的霸道和僭越而涣然冰释了。尔后,周王室和郑国互相愈发疏离、厌恶,两边反目失和的时刻,行将到来。
诚然以割取王室稻麦的花样来玷污、挑战了王室,但郑庄公当前毕竟还是王室的卿士,为了不给其他诸侯借机过问、问罪郑国的话柄,郑庄公沟通再三,还是于周桓王三年(前717年)主动前去雒邑,朝见周桓王(意旨道理是行家都退一步,不要把关联搞得那么僵),这亦然周桓王继位后,郑庄公初次朝见皇帝。
但周桓王对郑庄公怨气不减,也不想让他陆续以‘王室卿士’的身份为郑国增添政事利益,于是在接见郑庄公时稀奇不对其加以礼遇,还出言讥刺:
“本年郑国的食粮得益怎样样啊,温邑、成周的稻麦,寡东谈主应该不错留着我方吃了吧!”
见周皇帝不顾身份出言讽刺,郑庄公当即愤怒,但又不可顺利和周桓王顶嘴(那样就失去了主动权,且在礼制上也落下风了),因此只可恨恨地忍了怨气,向周桓王告辞归国。而周桓王对郑庄公既不赐宴、也不馈赠(这都是诸侯朝见皇帝时,必须完成的礼节),只是派东谈主送了十车黍米(黄米)予郑庄公,说是给郑国将来遇到灾难时济急用。
先是讥刺郑国‘偷粮’,然后又吊唁郑国会遇到饥馑,周桓王的一坐一谈,透澈激愤了郑庄公。因此,郑庄公决定公开将这十车黍米退给周桓王,我方则巧合离开雒邑,今后再也不来朝见这个“尖嘴薄舌”的皇帝了。
但随同郑庄公朝见皇帝的郑国医师祭足却合计这样作念的话,会导致诸侯借机针对郑国,于是劝谏郑庄公此时不要意气用事,还是收下皇帝的犒赏,不可让诸侯们看见郑国和王室的公开矛盾。
赶巧这个时候,王室卿士、郑庄公的同寅周公黑肩(周桓公)前来访问,并以皇帝的方式赐给郑庄公两车彩缯(织品),以慰问郑庄公(周公的意旨道理是居中统逐个下,不要让王室和郑国就此冲破)。
祭足见状,立即劝郑庄公将机就计;将机就计,收下两车彩缯,然后将缯帛袒护于皇帝所赐的十车黍米之上,再配上私制的‘彤弓弧矢’(皇帝赐器、用于授诸侯用兵之权),由雒邑城门一齐招摇复返郑国,还声称这是皇帝的厚赏,并授命郑国兴师挞伐不敬王室的宋国:
“宋国不尊王室、久不朝聘,实属不臣之谈;皇帝已命郑国代为问罪于宋。”(其实,郑国才是阿谁不尊王室的‘不臣’。)
尔后,郑庄公就‘假传王命’,约都、鲁两国一谈伐宋,克宋国郜、防二邑,大北宋军,所获颇丰,郑国的国力也由此更强;而周皇帝许久之后,才得知有此事。
郑庄公被周桓王讽刺、讥刺,离开雒邑之后,周公(周桓公黑肩)曾对周桓王劝谏说:
“咱们周室之是以粗略告成东迁,所依靠的助力,等于晋国、郑国。即使对待郑国亲近而友爱,用以饱读舞其他诸侯能像郑国一样尊奉王室,尚且还怕诸侯们不效仿,何况咱们这次对郑国实在是太霸道了;生怕郑伯(郑庄公)经过这一次的鄙视后,不大可能再来朝见皇帝您了。”
周桓王正想找个契机将郑庄公赶出王室卿士之列,生怕他厚着脸皮占位置不肯走,那儿还肯礼遇郑庄公;因此,周桓王根底不听周公的敢言,尔后对待郑国依旧还是(不外郑庄公也确乎厚着脸皮没主动离职)。
诚然陆续占据着周室卿士(司徒)之位,但郑庄公对周皇帝的归罪却少量儿也没减少;周桓王五年(前715年)春天,郑庄公因归罪周桓王对我方的不礼遇魄力,于是向鲁国苦求以泰山隔壁的郑国祊田(山东费县以东约三十里),与鲁邦交换许田(今河南许昌以南),以示郑国以后不再祭祀泰山、改为祭祀周公(周公旦),这等于在稀奇向周皇帝请愿。
合并年,在都僖公的统一下,宋国、卫国与郑国再行修好,三国国君于温邑会见,并在瓦屋(河南温县以西)达成盟约,暂时放手之前的旧恨。为了暗示我方的事迹、以及杰出我方‘王室卿士’的身份,八月,郑庄公主动指点都僖公往雒邑朝见周桓王,呈文这次盟会的恶果。
也等于在这次接见都僖公中,周桓王才得知郑庄公竟然假传王命,暗里攻宋。于是,冲冠发怒的周桓王在免强完成接见诸侯(都僖公)的礼节经过后,就第一时辰任命虢公林父(具体身份不祥,或为虢公忌父之子)为王室右卿士,以分郑庄公之权(郑庄公之前是卿士,当前改为左卿士)。
在我方(于王室中)的地位被周桓王均权、收缩后,郑庄公愈加不屑于尊奉王室,尔后接连数年都不前去朝见、贡聘周皇帝,以尽臣子的服务;在此技巧,郑庄公还赓续兴师与宋、卫、蔡、许诸邦交战,夺取了大片地盘,又和都国、鲁国国君几次会盟,将‘世界共主’的周皇帝抛到了一边。
周桓王十三年(前707年),因为郑庄公久不来雒邑朝见,又不肯主动烧毁王室卿士的身份(以此政事身份、不错陆续行扩大郑国影响之事),周桓王不宁肯再受郑庄公的欺瞒和薄待,按纳不住之下,便公开晓示免去郑庄公的右卿士之位,王室朝政一委虢公林父。
而得知此过后的郑庄公,与王室的鉏铻矛盾愈发敏锐,天然不可能垂头服软、前来朝觐皇帝,主动向皇帝认错。周、郑之间的纠纷因此愈演愈烈。
得知郑庄公依旧握‘拒不认错、死扛到底’的毅力魄力后,为了崇尚王室的尊容和皇帝的好意思瞻念,周桓王决定亲率王师六军伐郑,还征调了与郑国有旧怨的陈、蔡、卫三国戎行,构成联军遑急郑国。
出征之前,为扩大公论影响,周桓王意气激越地公开责骂郑庄公之罪:“寤生(郑庄公之名)霸道、欺寡东谈主太甚!若不讨之,诸侯或灵验尤。寡东谈主当亲帅六军,伐郑以讨寤生其罪;寡东谈主与寤生誓不两立!”
那时,陈国刚刚发生内乱——陈桓公弃世后,其弟令郎佗杀桓公太子免自强,即陈废公;陈国国东谈主不屈陈废公,纷繁逃离,陈国因此东谈主心不稳,戎行也莫得士气。但周皇帝亲口征召兴师,陈废公不久,地位不稳,正需要皇帝的招供来踏实我方的君位,于是不敢违命,只得免强召集戎行,以陈医师伯爰带领,随周桓王及王师向郑国进发。
其他蔡、卫两国,也各自调派戎行从征。周桓王将联军分为全军,命虢公林父率右军,佐以蔡、卫之军;以周公黑肩率左军,佐以陈军;周桓王则自率六军主力为中军,各军傍边接应、共同伐郑。
郑庄公在新郑听闻周皇帝切身率军前来挞伐后,诚然对此事早有料想,但心里其实也有些没底,于是召集诸医师照拂,酌量如何唐突。那时,医师祭足忽视遣使谢罪,转祸为福;医师高渠弥忽视固守坚壁、以待王师意怠,再谈战和,不外这些倡导都被郑庄公所否决。
终末,是郑医师子元(郑庄公之子令郎突,将来的郑厉公)进言:
“这一战,是以臣敌君,于理不直,于法不对,只可快刀斩乱麻,不宜迟缓,久拖未定必将生变。王师三分,则我军也应以全军唐突;我军出战后,傍边两军结为方阵,叛逆王师傍边两军,君上自率中军,以抗皇帝。陈佗(陈废公)弑君新立,陈东谈主不从者甚多,这次免强从皇帝征调,其军势必钩心斗角、少有战意。我右军先击(王师左军中的)陈军,陈军势必不敌而奔逃;再命我左军袭(王师右军中的)蔡、卫两军,其闻陈军战败,亦将阵崩溃退。然后,合全军之兵攻王师中军、逼退皇帝,必定无往不克!”
郑庄公听完子元的进言后喜出望外,当即接受了他的忽视,并让郑太子曼伯(即也曾赴雒邑为东谈主质的令郎忽,将来的郑昭公)带领郑国右军,祭足率左军,我方则率原繁(郑国公室、郑庄公庶兄或者堂兄)、高渠弥、瑕叔盈、祝聃等郑国医师直领郑中军,说合出迎王师(对战)。
出战之前,高渠弥又向郑庄公献阵法——以二十五乘兵车为偏,以甲士五东谈主为伍;一偏在前,甲士五伍随后,塞偏之傍边罅漏。车伤一东谈主,伍即行补缺,频繁保握车阵竣工、且济河焚舟。兵阵因此极坚极密,攻守恬逸难,号为“鱼丽阵”(就像鱼的鳞片一样层层相扣、各自呼应)。对此崇高的阵法,郑庄公天然不会终止,于是便接纳高渠弥的献计,以‘鱼丽阵’迎战行将到来的王师和陈、蔡、卫联军。
此时,周桓王亲率的王师联军如故插足郑国境内,郑庄公出头露面,也亲率郑国全军出新郑,以‘鱼丽阵’迎战王师;两军相会于繻葛(河南长葛以北),大战一触即发。
周桓王正本以为我方以‘皇帝之尊’亲率王师出征、‘以讨不臣’后,郑庄公会忌惮失措,乖乖地俯首认错、并出迎谢罪;但没猜度郑庄公竟然涓滴不怕惧皇帝威仪,不但不向皇帝垂头,还主动兴师叛逆王师,实在是胆大泼天。
被郑庄公如斯嚣张霸道的魄力所激愤的周桓王,于雷霆震怒之下,筹算切身驾车出战,以狠狠造就傲头傲脑的“乱臣寤生”;不外,王室卿士虢公林父知谈皇帝果然切智商有几把刷子,于是力谏劝止,总算拆除了周桓王的切身出阵念头。
崇拜对阵之前,周桓王准备了一大篇降低、训斥郑庄公的‘王命’,就等郑庄公出阵迎战时,马上将其痛骂一顿,以折郑军的锐气。但郑庄公诚然参与了切身布阵,可等于不出头向王师遑急,只是严守己方军阵,并传令其余两军:
“不可妄动,只仔细温文中军大旆(大纛、军中帅旗)的展动情况,得军令后再一同进兵!”
王师这一边,周桓王命东谈主几次出阵挑战,但郑军只是信守不出,并无应战。两边相握到午后,联军方面各军都懈怠窘迫,阵型慢慢松动繁杂;此时,郑庄公猜测王师的士气已泄,于是命瑕叔盈摇动中军大旆,郑左、右二军则随中军大旆的摇动指挥而一都鸣饱读进击。
如雷的饱读声中,郑太子曼伯(太子忽)率郑右军杀入王师左军,先膺惩士气涣散的陈军;而陈东谈主早就失去了斗志,遭受郑军膺惩后便一哄而散,四处奔逃,反将王师的阵地冲垮;王师左军统带周公黑肩截止不住溃军,又被郑军围攻,于是大北而遁走。
与此同期,郑左军主将祭足也率军杀入王师右军,只照着蔡、卫两军的旗帜突击,两军一样士气不高,勉力叛逆一阵后,也烧毁了对战,各自寻路退走。祭足再攻王师右军中的王室戎行,但王师右军统带虢公林父临危不乱,接力拘谨军阵,作念好了防护准备,祭足也不敢强行进逼,虢公林父得以率剩余王师右军缓缓退兵,要与周桓王的中军会合。
但王师傍边两军大部分都败阵溃散,溃兵还急不择途,冲击了王师中军的军阵;因此,周桓王的中军也立阵不住,欺压地后退。此时,郑庄公收拢契机,命原繁率郑中军猛攻王师中军,而太子曼伯的右军、祭足的左军也按照旗帜的指挥,合围王师中军。
郑国全军如墙而进,‘鱼丽阵’势不可挡,周桓王见败局已定,无奈之下只得传令退兵,并切身驾车断后,且战且退,迂缓郑军的追击。
激战中,郑国医师祝聃英勇作战,冲杀在最前,远眺望见了前线王师阵中的皇帝绣盖,知谈一定是周皇帝本东谈主的地点。于是祝聃飞快驾车靠拢,并睁大眼睛觑去,看准了皇帝的身影、致力于一箭,正中周桓王的左肩!
亏得周桓王身披的甲胄坚厚,因此所受箭伤不是很重,还不错陆续作战。祝聃本想驾车再次冲击皇帝的车驾,危险时刻,虢公林父实时赶到,退却了祝聃的膺惩、稳住了王师的阵地后,护卫着周桓王撤离,脱离了和郑军的斗争。
得胜后的郑庄公,也不肯意落下‘伤害皇帝’的罪名,于是在祝聃等东谈主条款陆续追击王师时,出言退却说:
“正人不但愿过分地占东谈主优势、欺东谈主太甚,更何况是侵凌皇帝;独一能挽回我方的抚慰,使国度免于消一火,这样就迷漫了。”
于是,郑庄公命令得胜收兵,莫得追打溃退中的王师。
另外,为了弥补‘误伤皇帝’的罅隙(其实是驰念与王室的对抗会引起其他诸侯的脑怒,乃至以此为借口针对郑国),郑庄公在休兵确当晚,就派祭足为使臣,携牛十二头、羊一百只,粟刍军资一百车当作慰劳王师的物资,连夜赶到王师大营内,以我方的方式向周桓王致书谢罪:
“死罪余臣寤生,不忍桓、武(郑桓公、郑武公)宗庙之陨,是以陈兵自保,非己愿也;奈军中不戒,至有犯王躬之罪,寤生不堪战兢之至;谨遣陪臣足,以为待罪余臣之使,敬问皇帝无恙;另奉不厚敝赋,聊作王师劳军之助,惟皇帝愁然,而赦余臣之罪!”
(打赢了再谢罪,既不损好意思瞻念,也给了周皇帝相宜的台阶下)。
周桓王此时箭伤未愈,心中对郑庄公咬牙切齿,本来不可能会接受郑庄公的谢罪,还想将祭足和他带来的‘慰问品’一谈丢出大营去,然后再搜集其他诸侯戎行,第二次挞伐郑庄公,以惩其冒犯王室、‘伤害皇帝’之罪。
但随同周桓王接见祭足的王室卿士虢公林父却想虑永久,巧合向皇帝进谏,合计此时如若再次召集诸侯伐郑,是“自彰其败”,将要为诸侯所鄙视;且世界有影响力的诸侯,大多与郑国相善(如都、鲁、晋),如果王室征召诸侯不至,岂不是徒遭郑国嘲笑。
而况,王室如今还有更紧要的事情要作念(指晋国公室发生内斗,曲沃与翼城两地相争,王室要相沿晋国翼城大量,对抗曲沃小宗),而郑国也如故遣使劳军谢罪,不错借此宽待郑伯(郑庄公),给郑国改过改过的契机(两边都有台阶下)。
听完虢公林父的敢言后,周桓王抚着箭伤良久不语,面色肃静,逐渐有羞惭心思。虢公林父见状,知谈皇帝已精心想松动,又圉于好意思瞻念不肯亲口搭理宽待郑国,于是应机立断,露面代皇帝回话郑使祭足:
“寤生既已知其罪,皇帝仁德,从宽待之,郑使可谢恩,叩拜皇帝!”
祭足闻言后欢畅无比,立即叩头再拜,然后永别周皇帝,再遍巡王师各军,赠给牛羊粮秣,逐个问安慰劳(连陈、蔡、卫三国戎行都有份)。至天光线,祭足才谢别王师大营,回返郑国。
至此,周郑“繻葛之战”,就在郑庄公的主动‘谢罪’之下,以这样一种不端的花样已毕了。诚然周皇帝方式上获得了郑国的‘臣服’,以及言辞谦善的‘告罪书’,但骨子上,周皇帝以及周王室的威严,在这场干戈中,如故透澈扫地。
“箭射周皇帝”,不光射的是周桓王的体格,也标记着“礼乐征伐自皇帝出”轨制的拆伙;祝聃在繻葛的一箭,透澈将外刚内柔的周皇帝‘世界共主’的泰斗给射落到尘埃里。
而继郑国之后,各诸侯大国都国、晋国、楚国,秦国先后兴起,春秋强国争超越霸、敕令诸侯,大权旁落的周王室非但无力征讨,还要仰仗霸主的保护、提拔,智力免强存身,皇帝之位,如故形同虚设;而大国争霸的历史,也才刚刚拉开序幕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下一篇陆续开云体育(中国)官方网站
发布于:天津市